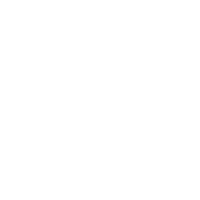欧文•亚隆
存在主义心理疗法和团体治疗大师
存在主义心理疗法最杰出的四大高手之一
当世仅存的国际精神医学大师
欧文•亚隆1931年生于华盛顿,是斯坦福大学精神病学终身荣誉教授,其主讲的录音带广泛使用于治疗师的训练工作。因其在临床精神医学领域的贡献,曾获得一九七四年艾德华·史崔克奖;一九七九年获得美国精神医学会为学术研究颁发的基金奖。
欧文•亚隆除撰写专业教科书如《团体心理治疗》、《团体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务》、《住院病人团体心理治疗》,与吉妮.艾尔金合著《日渐亲近》,与李伯曼和麦尔斯合著《会心团体:最初的事实》之外,亚隆也擅写心理治疗小说和故事,如《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》、《诊疗椅上的谎言》、《当尼采哭泣》、《生命的意义》、《爱情刽子手》、《叔本华的眼泪》等,多次荣获欧美小说和非小说文类奖项。
同欧文•亚隆对话,对国内从事团体咨询与治疗的专家学者而言无疑是一次难得的交流、沟通和学习的机会,因此我们力邀大师--欧文•亚隆进行视频直播,举办“与大师同行—对话国际团体治疗大师欧文·亚隆——暨美中团体心理咨询与治疗高峰论坛”,同时也为国内同行提供一次正式的交流、沟通和学习的平台。
此次论坛邀请了国内最专业、最具权威的团体咨询治疗专家、学者、拥有丰富治疗经验的心理科临床医生,齐集一堂共举盛会,探讨团体治疗在中国的现状、发展前景及方向。论坛的目的旨在推动中国团体治疗的发展,使团体治疗广泛应用于各大中小院校、医院、社区等方面,缓解国内心理咨询服务极其短缺的困境,推广效率更高的团体咨询方式,培养更多优秀团体治疗师,开拓广阔的自我发展空间。整合国内外先进的心理治疗资源,推动团体治疗在中国的发展,于中国心理学界有重要的意义。
与欧文•亚隆的对话:
柏晓利:亚隆先生,请问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您成为如此优秀的团体治疗大师?
亚 隆:我开始进入医师培训时,有一个老师叫弗兰克,他是最早期的团体治疗师之一。我从开始就被告知团体治疗是非常有力量的。很多年前,我们更多感兴趣的是弗洛伊德的思想,他研究的焦点在童年早期,主要是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。对我来讲,改变你和别人关系的方式,可能就是团体治疗方式,是比较好的可以看到人和人如何建立关系的模式。
柏晓利:在我们的书信往来中您提到存在心理治疗,能不能在这里讲一下您如何将存在心理治疗的精髓应用到团体中?
亚 隆:我想讲讲存在主义的治疗问题,我建议大家简单地想想自己的存在,把自己生活当中的干扰放到一边,比如手机、电子邮件等等。我们来反思一下自己的存在,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深的担忧。《存在心理治疗》聚焦于很多专门的考虑或终极的忧虑,比如死亡。我们在这本书里面就可以知道死亡就是一个终极的忧虑,或者说生活的意义、目标是什么。对于我们来讲,人类似乎是一个需要意义来生存的动物,我们是被困扰的,如果发现生活是毫无意义的,对我们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还有一些终极的考虑和关切,比如孤独感。这是我的两个不同兴趣,一个是团体治疗,一个是存在主义治疗,是两方面的问题。
樊富珉:您觉得团体治疗特殊的功能是哪些,我们会有哪些收益,实现团体治疗成功的重要因子是什么?
亚 隆:我们应该用复述的形式来说团体治疗,有很多团体治疗的取向,比如非常短期的应急和创伤的团体治疗,主题是哀伤,可能只用几个小时;还比如针对地震幸存者的治疗也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。还有就是酗酒者治疗、无领导的团体治疗、近视障碍的治疗,也是这样的团体。我看到还有很多带领癌症治疗小组的,病人知道自己必然要面对死亡。在我们国家,病人住院时间只有一到两周,所以小组成员每天都会见面,因为不同的人会进入医院,每天小组的组成也会不一样。一个持续3年至20年的长期小组,其治疗目标是很有野心的。我们确实想改变人们如何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,这是我们的目标。我回顾了一下各种各样的团体治疗形式。所以说,你需要先说出是什么样特定的小组。
我带了一本书,这是《团体治疗的理论和实践》。我花了很多年写这本书,在美国,过几年我就重写一遍。这是在美国的一版,我花了大概10—15年的时间来写这本书。我组织这本书的方式,其实就是刚才大家提给我的问题,问团体治疗是怎么帮助来访者的。我们帮助别人的方式是,不同的团体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来访者,这本书就是探索方法。比如说,我们在团体当中普遍性的因素,他们明白他们的问题不是自己独有的,其他人也有,其他人有相同的思想和相同的经历,这样你就会觉得自己不再孤独,或者其他人都会觉得能获得知识,他们被团体接受,是这个团体真正的成员。这就是团体治疗。
柏晓利:亚隆先生,您认为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才是有效的。
亚 隆:精神分析是弗洛伊德核心的工具,病人每周在躺椅上躺几次,这种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心理治疗的需要了。我的很多同事都会在培训当中接受个体的咨询,我在精神分析上花了700小时完成我的培训,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工作方式。所以,渐渐地我们进入了短期治疗的模式。今天,我们通常会一周一次治疗,有时候一周两次,当然还有团体治疗,我觉得团体治疗是一个非常有力量和非常重要的方式。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,团体治疗不仅仅是经济上省力,一个治疗师可以带7个病人,它还可以提供个体治疗不能提供的东西,你可以在团体中知道怎么和别人打交道,以及你为什么不能和别人建立关系。
柏晓利:在小组治疗中,治疗师和病人的关系是什么,您在说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。但实际上,他们的关系不可能是平等的。您能就这个问题解释一下吗?
亚 隆:大多数的病人来我这里之前,已经接触过其他的治疗师,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效果。几乎每个人都是因为治疗关系的缘故导致治疗失效。他们认为治疗师或者是太疏离,没有感情,或者是他的感情隐藏得太多。因此,我会跟我的病人有更紧密的联系,病人问关于我自己的问题,是否结婚、读什么样的书,我会回答。在谈到存在治疗的时候,显示更多的证据,病人跟我在生活当中有同样的应激和压力。所以我对我的病人就表现得更为开放一些,我会说一些关于自我暴露的问题,这是关于治疗工作的暴露。
柏晓利:如果病人问,这个治疗对我有什么帮助呢?
亚 隆:对这种问题,我们要非常地坦诚,我可以告诉他关于治疗是如何起效的方法。如果在团体当中治疗,团员问我治疗的目的是什么?这个治疗怎么帮助我?我就会告诉他们,我会把我所知所想全都真实地告诉他们。你之所以到这个小组来,是改变你和别人建立关系的方式。
柏晓利:《团体心理治疗的理论与实务》我们很多人都读了这本书,在这本书里有一个问题,15次的高度结构化的小组,可能很多人没钱参加很多次的组,大概15次是比较高的极限了,您能介绍一下短期的高度集中化的小组是如何操作的吗?
亚 隆:我不知道这跟长期治疗在工作方式上面有什么区别,你在一开始的时候,可以告诉病人,我们这次治疗有15次,我会想办法知道每个病人的目标是什么,告诉他们目标,并提醒他们这些治疗的目标。我会关注病人的治疗到了什么样的进展,我也会注意每一个个体在治疗过程中的目标是什么。
柏晓利:在中国团体治疗发展还是处于一个初期阶段,您建议我们如何去培训临床团体治疗师?
亚 隆:有三种方式,第一种方式是观察。观察其他治疗师的工作,所以我经常会让我的学员来观察我的团体,这个时间通常是一年。有时,和这些学生讨论这些问题,然后让我的病人观看,我的病人也参与这个对话。
另外一个方式是读书。
第三种方式就是参与治疗性团体。你可以领导一个由学生组成的小组,在美国非常常见,每周来做这种训练。我让我的学生加入到其他团体的治疗当中,学生本身不是病人,但是以一种展示自己的方式来进行工作的时候,彼此提供对方一些反馈,可以找到一些机会进行治疗。我再讲一下团体培训的事情,要有一个督导,在学生实习的时候,督导在后面看着,每周我会让督导去看看,然后几个月以后,这个学生就可以独立进行了。对于所有治疗师来讲,个人的经历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觉得任何一个团体治疗师都必须要花时间来处理自己的问题,你们要从病人的视角来看问题。我认识的所有好的治疗师都有这样的经历,没有一个不是。
孙时进:亚隆先生,这么多年来,社会的经济变化使好多人的人际关系发生了变化。我们是让来访者适应各种变化还是其他?比如一个企业,训练自己的员工适应不合理的关系?
亚 隆:这个问题也很好。从弗洛伊德的变化到现在,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平等的关系。但让人们看起来,像是这样的人改变了现状。我是一个治疗师,不是一个尝试社会改变的人。也许在团体当中,有很长时间的静默。你会发现在同一个时间有不同的反应,同样一个刺激不同的反应。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内心世界。所以在这个团体当中,一个刺激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反映,这就意味着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是切进或者是接近团体的事件。比如在工作当中,有很多人对工作不满意,可能有一个非常有启发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内部世界是什么样的。为什么是他的内部世界让他作出这样的反应呢?如果所有的人对这个事件有同样的感受的话,那么这个环境是需要社会变革的。
曾奇峰医生:能不能请您以在团里面的那种真诚,说一下今天早晨谈话的感受。
亚 隆: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第一部分,我非常感动。语言是一个重要的问题,在后面的10或15分钟的时候,我看到了更加丰富的表情。我现在就看到了一个穿粉色上衣的男士和很多的表情,我觉得和大家走得更近了。这是我回答刚才问题的一个方式,越到最后离大家更近了。第二部分,对我来说,很痛苦的是你们问问题的时候我没办法给予更多的回答。我觉得大家有非常珍贵的要求,就是想得到知识。我希望我能够以团体的形式跟大家在一起,这样我就可以给大家更多的东西。所以我感受到一种无助。还有一种感受,就是我要搜肠刮肚,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你们。我还有一个愿望是可以马上到达大洋彼岸,给你们做团体咨询师的培训。
版权所有 © 2025 广州心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备案号:粤ICP备2020114672号-1 技术支持: 方孔网络